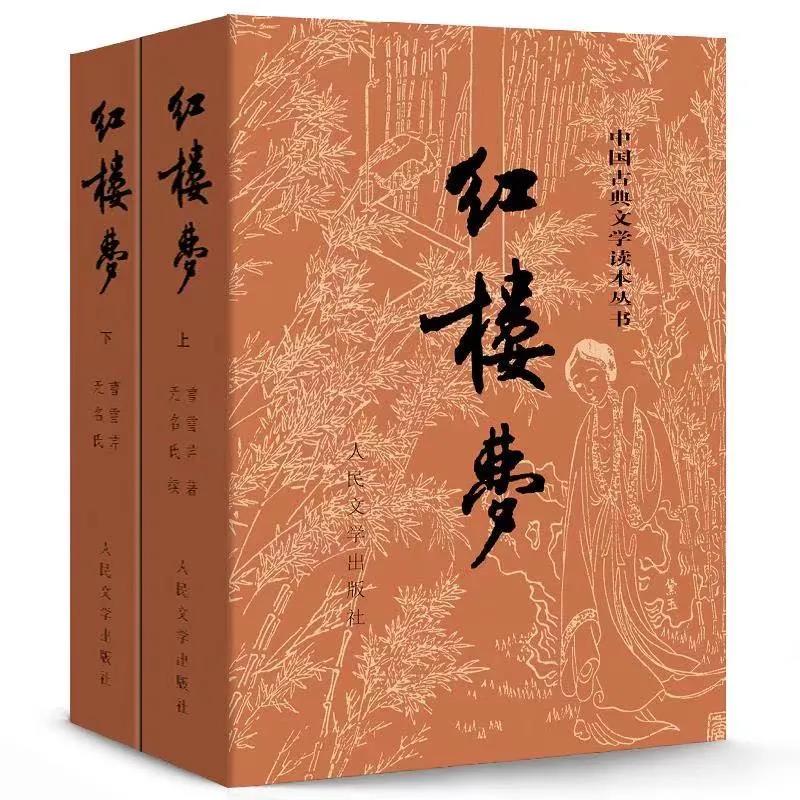小时候虽有拜读《红楼》多次,但只是囫囵吞枣,浅尝辄止,即使到如今,仍觉得自己孤陋寡闻,知之甚少,了解颇浅。初抚书页,再遇87年影视,总一种隐隐的奇妙的感觉,仿佛心灵相通,仿佛回到那段韶光,那段属于清朝的记忆。我只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,真的可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吗?世俗多牵绕,真的可以全身而退吗?青灯古佛,了结残生,种种疑惑,萦绕在心头,挥之不去。点一支香,一本佛经,一曲《幽兰操》,细细回味《红楼》中那与魏晋的渊源。若言红楼,吾必思魏晋。多想穿越回到那个年代,或是酒色,或是药石,或是丝竹,或是山水,或是我的心,亦或是我无处安放的灵魂。
余意中之佳士乃阮籍,意中之佳人乃黛玉。潇湘命途多舛,红颜薄命,吾不禁为之唏嘘。一生只为一段情的她一生挚爱一个人,一生只怀一种愁的她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休。他狂放不羁,恣意潇洒,一种风流。名士也难免多情,心有猛虎,却细嗅着蔷薇。此二者必有其相通焉。虽其人物时代相异,然内中形神,若合一契,皆归于情。余独爱其如“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。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。
余英时先生尝云:“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,基本上是属于魏晋反礼法的一型。这一型的思想在理论上持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对抗,在实践中则常表现为任情而废礼。《红楼梦》中的‘情’字无疑是‘礼’字的对面。‘情’出自然,‘礼’由名教;所以魏晋时代哲学上的自然与名教之争落到社会范畴之内便是‘情’与‘礼’的对立。所以换一个角度来看,《红楼梦》中的两个对立的世界其实也就是‘情’世界与‘礼’世界的分野。”越名教而任自然,此曹公与魏晋诸贤之相契合也。
宝玉好在女儿堆里厮混,厌世俗之陈礼,非不通人情,乃厌虚伪而重真情。此点于蔑视礼法之魏晋士人尤显。阮籍丧母,不拘俗礼,对弈如故,饮酒三斗,举声一号,呕血数升。虽不循礼,真情在焉。《红楼梦》着意者乃“儿女真情”,贾宝玉任情适性、不顾世人诽谤的“痴”,颇有嵇阮之辈不合时宜之味。宝玉所悼者乃佳人之去美之凋零,乃其对美好人物的深情,其形与阮籍之痛哭不相识之兵家女何其相似,岂得谓私情哉?
宝玉情之所钟,非唯于人,亦及于物,情不情者,非唯情于有情之人,亦情于无情之山水丘壑、花鸟虫鱼,于世间美好之人与物。宝玉调脂弄粉,痴心呆意,与芳官醉眠同榻。爱红成癖,恣情任性,依然故我。此种情态,同阮籍醉后随便眠于邻妇之侧,漫不经心,并无他意,有何异哉!故曰,率真任性、不拘形迹之形,乃其具魏晋人风貌之因也。
而《红楼》之超于《世说》者,盖世说以女子为宾而红楼以女子为主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作者开篇自云: “今风尘碌碌,,一事无成,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,一一细考较去,觉其行止见识,皆出于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须眉,诚不若彼裙钗哉?实愧则有余,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!”及后文宝玉“女儿是水作的骨肉,男子是泥作的骨肉,我见女儿便觉清爽,见男子便觉浊臭不堪”之言,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也。
红楼诸钗,尤以黛玉湘云二人最具名士风度,使为男儿身生于魏晋,嵇康阮籍辈必当求把臂同游于竹林也,所差者,唯酒量不及耳。一个居于潇湘竹苑,凤尾森森,龙吟细细之所。一个越名教而任自然。此二者想亦有遥通焉。探春曾言:“孰谓莲社之雄才,独许须眉;直以东山之雅会,让余脂粉。若蒙棹雪而来,娣则扫花以待。”何等气概,我等只能望其项背。其惜大观园中“些山滴水”“林木泉石”,庶几与晋人山水之情相通,颇有晋人风味。
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?个体自由与大慈大悲在红楼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悟澹法师说,《红楼梦》真的是一本“应无所而生其心”的经书,这是一本像镜子一样的小说。“竹影扫阶尘不动,月穿潭底水无痕”就是对《金刚经》这句话最好的解释。为什么有人会讨厌书中的某个角色,为什么有人会欣赏书中的某个角色,原因很简单,因为在《红楼梦》这本世间的经书中,有你的倒影。黄粱一梦,然后如梦初醒,最后大彻大悟。人生不就是一场开悟的梦吗?犹记得阮籍与大师的那一对望,虽相隔甚远,却如近在咫尺。“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柄神导气之术,登皆不应.籍因长啸而退,至半岭,闻有声若鸾风之音,响乎岩谷,乃登之啸也。”籍顿悟,夫大人者,乃与造物同体,天地并生,逍遥浮世,与道俱成,变化散聚,不常其形。遂归。 镜花水月,断井颓垣,原道是姹紫嫣红开遍。 宝玉也顿悟了:“凡有所相,皆是虚妄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。”
不知是谁作歌道:
“我所居兮,青埂之峰。我所游兮,鸿蒙大空。谁与我游兮,吾谁与从?渺渺茫茫兮,归彼大荒。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,并无一人。”
始从何来,终回何去。不过是回去罢了。